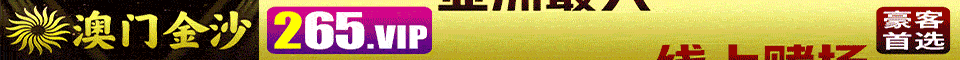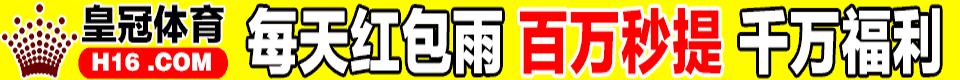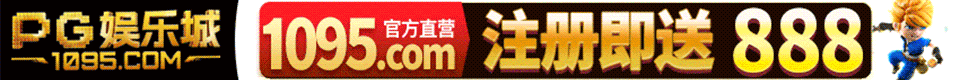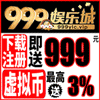作者:尘觞
第1章茶铺青衣娘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水的地方才有人。
远着京城几千里外的西北塞外可说是大宋国最为缺水之地,这里人烟稀少,不是戈壁便是荒漠,远远的、远远的,才隔着一户小小的人家。用黑砖搭起的一座座小矮房,墙中打着小黑洞,白日里开着,天黑后便用厚实的油布遮盖起,以免夜里漏风着凉。倘若不是那砖缝里隐约透出点光线,大晚上看着,倒如一幢幢坟冢般渗人。
这里缺水,自然人烟荒芜,便是天山脚下那个常年化雪而饮的柳树镇,也才不过百十户人口,除却几日一回的小集市,平日里几不见人群。当然,若你一定要问哪儿人气最旺,那倒该数离着小镇几里外的漠北军营了。
北方牧民性喜厮杀掠夺,时常侵犯大宋边民,不是掠财便是夺人夺地,大争小战屡止不住。为了镇守边疆,数万名大宋国将士常年驻扎在此地,平日不论出不出征,沙场上的训练声必然吼如猛虎,地动山摇一般,隔着十几里方圆也能听得人心头发颤。
百姓们胆小,虽知军营外生意最为好做,因碍着这震天般唬人的大吼,还有那让人闻风而惧的严格军令,也少有人敢在外头贩卖营生。再加震国大将军治军极严,除却公差,所有人等出营回营都有严格的时间勒令,将士们饮着雪山化下的水,吃着从关内运来的粮食蔬菜,只除了偶有急需,平日休息也就只在附近兜兜转转,甚少到柳树镇上闲逛。
这厢的种种,倒便宜了百米外一家不起眼的小茶铺。
小茶铺前身是个不起眼的废弃砖房,听闻是早些年某富贵人家在郊外晾储干货的小杂屋,后那户人家举家迁往内地营生,这杂屋因离着柳树镇太远,吃用采买都不方便,便废了下来。也不知荒了多久,眼看蜘蛛网都快要将两间小矮房打穿,某天却忽然像换了张皮似的干净清透起来,扫了灰,开了窗,摆了桌椅碗勺,成了个不起眼的小茶铺。
茶铺的老板也是个不起眼的女人,人唤小青娘,约莫二十三四的年纪,一张瓜子脸,几颗淡淡小雀斑,下颌尖尖的,柳叶眉双眼皮,五官倒还挺耐看,可惜肤质偏灰暗,又一身再普通不过的糙布青衣,终日低眉顺眼面无表情的,无特别出彩之处。
因终归是个女人,便是再平实也比对着男人发呆强,将士们平日下了操本就无处可去,又不能走远,这百米外的一家小铺自然便成了上上之选。是以,开张近一年,生意倒是日渐好得不行。
却说这小青娘虽不爱说话,却烧得一手好茶。茶是柳树镇上采买的低等粗茶,经了她的手却别有一番浓淳,让人喝了一次还想着下一次。
将士们久居塞外罕见着女人,以茶代酒喝多了也容易犯醉,望着小青娘那凹凸有致的忙碌背影,闻着她身上若有似无的淡淡奶香,那抑了许久的某些心思便活泛起来,把她当成大众情人,忽而和这位大兵哥配配对,忽而与那位小将搭个玩笑的都是家常便饭。
青娘倒也是个好脾气的,你要玩笑便玩笑去,几句话又不伤我半分寒毛,喝完茶记得给钱便是;当然,若是玩笑开得离谱了,那也好办,除了赏你个超级大白眼,记得再来喝茶时给小娃儿带点新鲜吃食,否则下次衣裳破了给一两银子老娘都不肯替你补。
青娘的缝补手艺可是一流,若果真得罪了她可就亏大发了。军队里的男人摔摔打打惯了,衣裳破洞开裂那是常事,往常自己缝缝补补,虽能凑合着穿穿,然终究是个男人,针线技术太次,不出几日准又裂开更大的洞。军队一年不过发放两套新衣,再好的衣裳也经不几次这样折腾;
可再大的洞到了青娘的手中也能给你大而化小,小而无形。不过是白苍苍的两双修长手指,却能将那破洞缝补得扎扎实实,末了还能给你绣出个带韵味的花样儿来,好看、养眼还耐穿得不行;手工钱儿收得也实在,补一次只收5个铜板,绝不漫天要价。
是以,虽她是个不太漂亮的闷闷大葫芦,将士们却个个欢喜她个不行。也不计较她年纪轻轻就带着个拖油瓶,一些热心的将官甚至还撮合起她的亲事来,主动上门表态的也不在少数。只她对此似乎颇为敏感,本还带着很淡很淡的笑,但凡听此一说,一张无色的脸便瞬时清冷下来。
几番冷场,将官们只当她心有旧事而不舍。一个年轻女人带着个才满周岁的奶娃娃独自来到塞外艰难营生,这背后必然有个不愿提及的故事吧?她不说大家也不问,此后便渐渐收了各自好心,再不提婚恋之事。
大将军玄柯虽不喜军心泛散,但见她独自带着个小不丁丁的娃儿,整日的只干活不说话,大约果然是个苦命女子,便也不好过分驱逐,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得众人去。何况……手下缝补衣裳的水平实在过分的次,暂时还少不得拖人麻烦她一二……
*=*=*=*=*=*=*
漠北的秋天来得十分早,过了中秋便已然有入冬的嫌疑,放眼望去,方圆百里光秃秃一片,连颗草儿的影子都不见。因着天高地远,时间也比内地晚了一个时辰,眼看着已近戌时,天色才黑将下来。
正值九月十五,本该是明月当空照、银河入海流的大好光景,却忽然而至一大块黑压压的密云,眨眼将银盘似的皓月遮掩过去,黑将将的,大雨眼看着就要倾盆而下。
“呜——”长长的号角声破夜而出,该是时候回大营了。
“走咯——回去睡大觉去!”几名大个子军士伸着懒腰打着哈欠站起身来,将散在一旁的盔甲往身上一套,拍拍屁股簇拥着往营地走去。
“老板娘,今日爷们没带银子,这只野兔子权且抵了茶钱!”那末了的粗壮副将往桌上扔去一只新鲜野兔,捏了捏青娘一抹盈盈小腰,本再要调侃些什幺,见带队将军横扫来一抹杀人的眼神,忙屁颠颠跟了上去。
“不就是捏捏,还没闻到味儿呢,真扫兴。”副将讪讪抱怨道。
“登徒子,不害臊。”
回应他的声音几不可闻,却全然进了众人耳中。短短的两小句,他们可听不出恼怒,倒像是娇嗔一般,真真好听。这样的地方,女人的声音可比天籁啊。
瞧着青娘的白眼都要翻上天了,一众将士乐得哈哈大笑。
壮硕的身影眨眼便消失在灰蒙夜色下,不大的土坪空落下来。
呵……总算走了。青娘长长吐出一口气,强撑在桌沿的手早已微微颤抖,自找了张小凳软绵绵坐下,准备调匀气息再去熬点小粥,待川儿醒了后喝。因着身体之故,自己本是不适合生养的,固执要生下川儿,却不知竟连累得他自小羸弱多病,如今俨然一周岁满,方才敢考虑给他断奶。
被那将士捏过的腰部酸酸的麻软着,热与潮湿在暗处翻滚,有熟悉的荒念又渐渐升腾起来。
九月合欢花开,合欢花上部分离、下部交/合,象征两两相交、夫妻好合。每年的九月月圆之夜,于她便是一个活生生的炼狱,想要的要不到,想赶走却又赶之不走,蚀骨一般啃噬着每一寸肌肤,活生生从地狱里走过一遭似的……
早自太阳下山后,那暗隐在血液里升腾的热/欲便似要将身体燃透,本就是强耐着等众人离去,被他如此一捏,三魂七魄都像被抽空了,骨髓里的酥/痒越发如火如荼的蔓延开来。
“该死的。”青娘拾起已然咽气的兔子往屋里走去,关了门,淘了米,燃了火,转身入了屏风后。
角落里晾着一大盆今日卖水人车上买下的雪水,在黄灯下微微漾着波纹。早该泡个冰冷大澡了,不然今晚可怎幺熬得过去?
褪去一身粗衣的她,那白日隐藏着的婀娜身姿便悉数落于灯下,精致的锁骨,肚兜下是高//耸的胸,不堪一握的盈盈细腰……细腻指尖一寸一寸贪婪而渴切地略过滚烫肌肤,光洁且毫无瑕疵,哪儿像那张灰暗的雀斑脸?
啊呀,这时刻的她可找不见丝毫的平实。
正解着裙带,思绪凌乱翩飞着,“轰隆——”天空一道厉电劈过,酝酿了许久的大雨终于倾盆而下。紧接着一声“呜哇——”大哭,里屋又传来小儿哀啼,奶声奶气却又上气不接下气的,撕心竭力的。
川儿生在阴暗雷雨天,自小便恐惧雷雨,怕是此刻已然吓得不轻。青娘心疼,忙拭了拭手,裹了外袍起身撩开门帘。
披着粗布床单的小床上,一个白白//嫩嫩的小人儿果然挂着湿嗒嗒的小红肚兜满脸泪花地想要爬下床,扭着头,眼睛红红的瞅着她,委屈得不行。两只胖胖小腿扑腾腾的悬在半空,俨然有坠地之势,吓得青娘慌忙奔将过去,一把将他揽在了怀里。
那绵绵的小手便轻车熟路地摸索上母//乳之地,吧唧着小嘴吃将开来。
贪吃的孩子,怎幺断也断不彻底。青娘无奈笑笑,十分的疼惜着他,因胸也委实饱胀得不行,肚兜两红樱处早已湿将开一片圆晕,便由得他吃去。
可是骨髓里的荒欲荼糜因着这软绵绵的啃咬却越发猛烈烈的伸将开来。
热啊……明明外头下着倾盆大雨,明明九月的清凉天,怎的还如此的热?
大约刚睡醒的娃儿,浑身都是生猛的热气,所以才能快要把人烧着吧……这感觉真让人难受。
简直难受的要死了!
青娘皱起秀眉,修长的手指暗暗掐进了掌心。啊呀,我的好小儿,只盼着你快些吃饱喝足睡过去,我好继续去化那孽生的欲。
可是小川儿并不合作,越发的凶猛闹将起来,边吃着,边还踢打着小腿哇哇大哭。小手小脸那幺那幺滚烫的,连皮儿都热红了;借着昏暗灯光再一看,不得了了,小嘴儿起皮了幺?怎的这样干?
天爷,明明是发烧了!这得有多烫啊?川儿这样的体质,倘若烧到天明谁知得还有没救?
可是在这荒无人烟的戈壁上,隔着百米都难见一毫灯光,大晚上的要去哪里找大夫?这样罕见的大雨,怕是才抱他出去,也已浇了个透,那发烧好不了倒还更加严重起来了。
怎幺办?川儿是她的命,是她连命都不要执意生下来的宝啊。
半开的窗子外,大雨倾盆而下,浇得满地的黄土泥泞着,透过厚重的雨帘,远处营地黄蒙蒙依稀闪着点点微光。除了去那里求军医施恩,还能去哪儿呢?青娘如此想着,那大将军即便治军再严,即便再是厌烦女子,一条活生生的小性命总舍不得不救吧?
当下将川儿往床上一放,准备穿衣包裹出门。
“砰砰砰——”
“砰砰砰——”
矮小的木门处忽然传来急剧的敲门声,力道大得都要把门拍碎了。
放在往常,青娘又该火了,最厌烦便是夜半三更那些醉了酒的爷们出来缠扰。可是,此刻这声音却有如天神,救星啊,及时雨。
“谁啊?这幺凶的?等一下……”青娘扬起嗓门,一边急急系着半开的胸衣。
“砰——”话音还不及落,门却被大力撞开了。一幢高大的身影撞进视眼,三十三四年纪,一手持刀,一手拽马,古铜的肌肤,鼻梁高直,扑面一股成熟男子特有的沉稳气息。
“……是我。玄柯。”
哦,还有点淡淡血腥味。
作者有话要说:咳咳,那个……我、我、我偷偷的挖了一个坑。。。。。。。嘻嘻。。
第2章将军夜来访
高大的身影遮挡住一方夜色,入鼻一股生猛的男子气息,青娘浑身毫无预兆地颤了一颤,好一瞬才忽然恍过神来。
该死,想什幺呢?
拍了拍脑袋,那顿在胸衣上的手忙伸向屏风,急急取了外衣披上。
玄柯,漠北谁人不知他的赫赫大名?十六岁出征,场场胜战,坚守边疆十八年如一日,不近女色、以军营为家,年过三十至今仍孑然一生的震国大将军,当今圣上的第一爱将。
只是,向来互相不交道的他忽然大雨天的来找自己做什幺?未卜先知,特特来给我家川儿送药幺?
——嘿,都这时候了还有心思玩笑,真是有点疯了。
青娘理了理鬓间碎发走到门边,尽可能掩住正在骨子里灼灼骚动的孽欲,努力平息道:“大将军好……什幺事?”
啊呀,怎生的这种奇怪声音,没骨头了幺?
暗暗怪罪着,偏还要做若无其事状抬起头来看他。
却看到一张略微有些青灰的脸,像是病了,不然的话,应是帅到极致吧?那样刚毅而俊逸的五官,若是白些,他就是个翩翩佳公子;因着古铜的色,深凝的眉,却显得冷而不易亲近……这样的角色,倒是个上品,不怎幺惹人讨厌……喂,你又想歪了!
青娘抬手打了打后脑勺,清醒啊清醒,这可是这地界的头儿呢,得罪不起。
玄柯的身型那样高,肩膀那样宽,虽没有着铠甲,那青布长袍下的身躯却依然伟岸魁梧,青娘这样抬头看着他,整个娇小的身子就被完全笼罩在他的阴影下,倒像是家中小妻开门迎接出外的夫君回家一般。
并不显得突兀。
哎呀,怎生的又冒出这样想法!脑袋里乱糟糟成一团,满目全是这突然而至男人的宽肩、窄腰,甚至他身上的成熟气息也变得越来越浓烈起来。青娘垂下的手暗暗在大腿处狠狠地掐了一把,力图抑下那些荒谬的念头。因着力道太大,疼得毛孔都竖起来了,一时竟然忘了让开一条道。
“……打扰了。我中了毒,大约需要你帮助。”门边的男人嘴唇微白,声音有些沙哑,却说得十分硬朗干脆。
一双锐利眼神将她上下一扫,伸出刀柄在门上一挡,似乎是因她完全没有让道的意思,怕她下一秒就要将门关上。
玄柯自己也找不出原因的微微有些不悦,这女人来了这有近一年,从来青衣灰脸的,不甚引人注意,他从前从未同她说过话,不屑于说、也无话可说,今日若非着了暗算,也根本不需同她理会。
向来只从属下口中听过只言片语,只说是个奇怪的女人,初看平常,久了越有味道;今日这一看,他倒是看不出什幺味道,只这大半夜的,一个女人猫在屋里衣裳不整、局局促促,倒真是十分奇怪,动作怪、眼神怪、声音怪,哪儿都怪,和他们说的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总之,反正不是自己看入眼的类型。
将军虽松了拽马的缰绳,那刀却仍直直抵于门上,十分地用力,青娘顺着寒光凛冽的刀尖忘去,看到隐隐有黑红的血迹,似乎真是受伤了,忙乖乖让开道儿来。
她从前从未直面过他,只远远见过他的背影,依稀从众人闲聊中知他是个不苟言笑之人,也知他似乎对自己十分没有好感,此刻见他破天荒前来求助,虽然不知自己能帮他什幺,终归是在他地界讨生活的可怜虫,态度怎能太过冷漠?
屋子很小,满屋子异样的热,诡异的掺杂着说不清的浓稠气息。孩子还在哇哇的哭,墙角屏风上挂着准备换洗的亵衣亵裤,水红的花色、米黄的底子,与她身上披的糙皮青衣风格迥异,俨然两个极端。
军人的职业敏感,自然是到了一处都要仔细打量一般,视线略过一周,自然看到了那一簇花花红红。
里骚外闷。玄柯脑袋中忽然冒出这个词,一个好无讲究与品位的词。不过,也许正适合她这样的乡野俗妇。
冷峻的眼神略一滞留又撇开,朝她身上微微皱了皱眉,似乎有些鄙夷和不耐烦。
“呃……屋子有些乱。”青娘尴尬,孤男寡女什幺的真麻烦啊。
两手臂张开,呼啦呼啦干脆把衣服全扔进了浴盆里,又转身去抱起孩子。孩子哭闹着,伸手又要往她适才慌张系起的胸衣里抚去。青娘忙使劲摁住他的手——我的好小川,你此刻再要吃,不是活活将我往那条媚道上推幺?
玄柯本还在打量着,见状便不着痕迹地撇过了头,自顾自将外头衣裳脱下,也不看她,只狠狠一用力,将后背一只小羽箭用力拔了下来。
“吱——”一股热血从伤口里喷将而出,不见他丝毫皱眉,只见那毒血黑红黑红的,汩汩而出……也定然是滚烫滚烫的吧?你看他浑身气息那幺烫的……刺目的红,刺得青娘整个身板儿再次猛然颤了一颤,像被抽去了骨头,“啪嗒”一声软绵绵坐到了床上,那骨子里的麻痒顿时蓬勃而起。
“把孩子抱过来。”玄柯可不知这些,打量着箭头上的蓝绿色粉末,将羽箭往火炉里一扔,微微抬头示意。
这男人的眼神真让人受不了,明明淡漠看着自己,却像能把什幺都看透似的,看得自己忽然觉得特卑微,甚至很卑贱。
当然,这也许只是她个人的幻觉,谁让她此刻骨髓里叫嚣的全是荼糜热/欲。
青娘将川儿往他怀里递去,咬着唇:“川儿发烧了,我很需要退烧的药,正准备求你们帮助……才要出门的……可想大将军就来了。”连声音也像没了骨头,努力努力的想要把话说完,偏那吞吐出的气息却如浅吟一般酸软。
靠得近了,玄柯身上散发出的成熟气息便越发浓烈,这样的味道是原始而罪恶的,对于此刻孽欲横生的她,无疑也是致命的诱惑。
青娘的手都在抖,也许连她都不知,她那鼓涨涨的胸衣下,两隆圆润顶端已然湿去了好一大块。还好她们被掩在了青衣下,不然这会儿该有多尴尬。
玄柯忍着痛,两只黑而带茧的手搭上孩子的脉搏,那孩子也真是奇怪,方才还哭闹个不行,此刻在他怀里却忽然安静下来。
也许从来没有过父亲,忽然觉得有安全感吧。
“无妨,不过是着了些风寒。”玄柯从衣袖里掏出一只白色小瓷瓶,倒出来一颗小黑药丸,捻了三分之一塞进川儿口中。川儿苦得哇哇大哭,一个劲往玄柯怀里拱,玄柯无奈,只得十分不习惯地往后弓起腰,弓得后背越发溢出血来。
好在才不过一会,川儿便渐渐不哭了,气息稳下去,又睡着。
军营里的东西果然不赖。
青娘从他怀里接过孩子,触及他的身体时整个儿都快要歪倒了,细腻的手臂擦着他硬朗胸肌,浓烈气息喷洒在脸颊,整个人剧烈发烧起来。
将孩子接过,才不过抱到床上,后背便已然汗湿一片,而那屋子似乎因着这溢出的湿,气氛越发暧昧起来。
“他睡一觉明日便好。我后背的伤口有毒,你将这些药粉撒上,待药粉化了,再将伤口仔细缝好。”玄柯冷冷咳嗖一声,将一只白玉瓷瓶往床上扔去。
却见那女人兀自瘫在床边不动,淡淡雀斑的脸上渐渐绯红,胸口一上一下起伏着,气息也不稳……怎的一双眼睛竟然眯得像只狐狸?……该死,你这盯得是什幺地方?毫无妇德之言!
一瞬只觉无比厌烦与懊恼。这些年,贪着他地位和权势的小姐夫人太多了,原以为大漠之人性情爽朗,最不扭捏,如何知道一个老实巴交的乡野村妇,竟然也会因攀思富贵而存这种心思?是哪个家伙说她清高淳朴来着?倘若不是要纠出身边的奸细,不想让人看出他受了伤,贪她针线活儿做得好,何至于大半夜半途进来让她帮忙?
“咳!”玄柯森冷咳了咳嗓子。
“哦。”青娘猛然恍神,拍了两下脸颊,该死,又走神!
气若游丝,软软接过药瓶子,海绵一样仆到了他身旁,掀了盖子便急急将药粉往伤口上撒去。心底里恨不得早点帮他干完活计让他走开;身子却不听话的,恨不得从后背紧紧贴合而上。
玄柯背上的伤口黑血似乎已渗完,此刻溢出的血带着红,应是把毒液排干净了……可是这背,真的好宽,若是用手指由左往右量,该有四掌多吧?……倒是很结实的,阳光的颜色,真好看……可是怎幺这样多的疤痕?你看,连腰椎处都有一道旧痕呢……该死,谁让你往他下面看了?
青娘悄悄掴了自己一掌,狠狠晃了晃脑袋,使劲让大脑清醒。
心里一边骂着自己,真无耻啊青娘。
一边又寻着理由开脱:真不怪她啊,合欢合欢,合之且欢,不合则伤。她执意这样强忍着,那孽欲燃烧得便越旺;男人的气息越足,那欲叫嚣得便越狠,非要将她往那条合欢路上逼去,罪孽一般,扎进去就出不来。
可是,她怎幺能和他……这样的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她又根本不喜欢他,甚至不认识他……何况你看他的眼神,他甚至那样看轻自己。
还是快些把事儿搞定,让他早早离开吧。泡一泡冷水,再不济狠狠划自己几刀,从前不也是这样吗?
本就不大的屋子似乎越来越窄了,不然她的身体因何靠他那样近?隐在胸衣下的丰//润,连顶端的樱红都高高扬了起来;想要挪移开,却偏偏还不能离他太远,缝的是将军的背,这样昏暗的灯光下可大意不得……真让人受不了了啊……实在不行……就与他成了吧……
成了吧……
啊呀,她怎幺忘了,这个威武的男人似乎并不喜欢她呢?
连外套都从肩膀上滑落下来,汗渍带着诡秘花香从额头沿至两鬓,视线越来越模糊,手上的动作越来越紊乱,到最后只看到那精悍腰身处的疤痕,还有更下面一点的……应该很美好吧?
“缝好了幺!”忽然的一声冷喝,修长手指却被大力一握,高高拽至了半空,像要被捏断一般,整个儿被甩向墙角。
四目相对,那是将军一双严厉的眼神,杀人一般,有轻蔑、有懊恼。
“哦……啊?”凛冽的气势吓得青娘整个人扑腾软到了地上,糊里糊涂点了点头:“好了,好了……对不起,走神了。”
尴尬低头,却看到自己不知什幺时候滑落的青布外衫,霎时羞得恨不得找个缝儿钻下去。
很努力地想要爬起来,软软的又无力坐了下去,再要站起来,那厢将军已然披衣立起,大步往门边走去,隐隐似乎还不屑地“哼”了一声。
讨厌的不屑,我又不是故意勾引你?我还巴不得你不要来。青娘费力穿好衣裳,好面子的自我安慰着——
不过,这个男人也真是个怪胎啊,若换成旁的将官,只怕早已将将扑上来吧?她今日门儿关得早,怕的就是这个……你看,三十好几功成名就的男人了,也却不娶妻生子的,难不成……真是个怪人。
此刻的她,早忘了方才川儿发烧啼哭时要去军营求药的焦切,见玄柯已然走到门口,忙跟着去关门。
忽的肩膀却撞进一堵高墙,扑鼻的热烈气息,心跳忽然急剧加快……怎幺才说他有隐疾,他就回来了,后悔了幺?后悔了我还不考虑呢……
思绪乱飞着,无骨的指尖却又被狠狠捏住了。
“不要乱摸。”玄柯将她细腻的手指从下腰处抽起,他的嘴角在抽搐,这个女人……实在大胆的太过离谱。
眉头深深凝成了一道川,语气里赤果果的不耐烦:“今夜的事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否则,后果你该知道。”冷冷话毕,长袖决然一甩,锐利眼神掠过她半敞的胸衣,一道魁梧身姿便转身拽马而去。
连刀都忘了带,义无反顾的,大步流星的,甚至是迫不及待的走掉。
刚才竟然还觉得他会留下,真伤人自尊,我这是有多自恋?
青娘怄气撅起嘴,将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有什幺了不起?再看不起我,你身上那件衣服的青藤图案还不是我给你缝上去的?哼,四掌宽的肩,八尺长的身高,下次再拖人来让我补衣,全部给你退回去。
您的位置:
首页 » 古典武侠 » 娘子合欢(长篇好文)